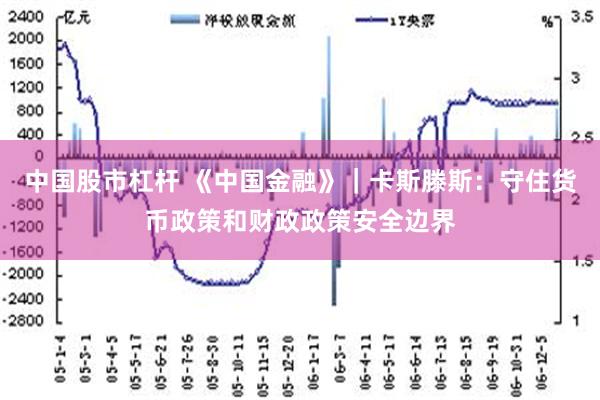
根据中指研究院测算,若按套均100平方米计算,货币化安置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可带动约1亿平方米住宅销售,对市场总量的贡献约为10%左右,这部分需求进入市场,有利于推动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100万套改造体量中部分需求有望在今年年底和2025年转化为实际销售,对新房销售将形成实质性带动。从改造体量上看,未来也存在进一步增加的空间。
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手段。我国资本市场也曾通过科技培育、并购重组支持经济产业转型,2013年—2016年互联网浪潮时期的创投市场和并购重组共同发展、2019年—2021年科创板与股权投资市场同步迈进等,A股市值结构逐步从金融地产向科技制造转型发展。
导读:“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无法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的上限或政策利率等简单指标来界定,它受到生产关系、金融市场结构等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作者|奥古斯汀·卡斯滕斯「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肖林译」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10期
“稳定区域”边界受到挑战
过去两年的金融市场非同寻常——通胀持续飙升,且具有突然性、全球性。许多国家的通胀水平已经达到几代人未曾经历过的水平。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近期出现的银行破产危机就是最突出的案例。高通胀和金融体系承压各有其具体的产生原因。但它们也反映出一个更广泛、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对“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形成挑战。所谓“稳定区域”,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支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同时,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外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单独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政策制定者每一次的政策选择似乎都是合理的。但这些政策效应日积月累地叠加在一起,却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境地。这提醒我们,经济体系可能从表面的风平浪静骤然转为风起云涌,而“稳定区域”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事后才会显现。
全球化等强大的长期推动力让我们忽略了一个曾经被视为观察政策是否偏离安全区域边界的关键信号——高通胀。持续低迷的通胀水平催生了一种信念,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平抑每一次经济衰退,并在几乎没有约束的情况下继续支撑经济的扩张。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都会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但在经济重拾增长时,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将政策回归正常化或重建政策缓冲的举措。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衰退之后,这一现象变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政策看起来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引发通胀,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总供给能够迅速适应总需求的变化。当疫情导致供给条件发生变化时,不知不觉间承担的风险就会表现得相当明显。
高通胀的产生
高通胀是政策制定者们面对的首要风险。高通胀已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且目前仍然处于高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通胀并不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退。
高通胀的成因有许多,包括疫情扰乱了商品供应链、疫情防控措施解除后支出的突然增加推动了对商品需求的快速反弹、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等。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期间实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刺激措施给通胀带来了更大的、更持久的且始料未及的影响。
疫情暴发后,许多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刺激力度已经超过了其GDP的10%——这种力度以前只在发生战争时出现过。与此同时,政策利率被降至零甚至负利率;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急速膨胀。在许多国家,家庭获得了大笔转移支付,甚至超过了疫情导致的收入损失。企业受益于慷慨的财政援助,也继续为在家休息的雇员保留职位并发放薪酬。在供给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导致需求快速增加,在推高通胀的同时,却对经济增长本身几乎没有效果。即便在经济复苏很长时间之后,刺激措施仍在继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所加码。
从当时来看,针对疫情的政策反应是完全合理的。这些政策维持了企业的运转,保障了民生,同时防止经济陷入混乱。在空前的困难情况下,采取的政策并不算激进。但也正因为极端情况前所未有,刺激政策的退出和调整变得极其困难。从事后看来,我们认为政策支持存在规模过大、范围过广、时间过长的问题。
在本轮高通胀开始抬头的时候,包括各国中央银行在内的多数观察人士预计,通胀上升只是暂时现象。许多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多次通胀飙升(通常是由油价上涨推动的),但最终总是会回落至较低水平。
但此次高通胀却不尽相同。尽管目前石油、二手车、航运价格比2022年的高峰期已有所回落,但价格更具黏性的服务业已成为推动通胀的主要力量,且劳动力市场依然吃紧。如果通胀不能在短时间下降,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此前住户和企业长期在低通胀环境中形成的通胀预期可能会发生转变,未来恢复价格稳定的成本将大大上升。政策利率可能需要维持在高于预期的水平上,且持续的时间需要更长。而这导致的后果显而易见:政府部门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即使在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区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也在稳步走高,而疫情期间的刺激措施进一步推高了债务水平。在高利率环境下,政府偿还债务的成本将迅速上升,公共财政的压力愈发凸显。
中央银行降低通胀的努力可能会受到多方面制约。在短期内,财政刺激措施会推高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抵消收紧货币政策的效果。IMF预计,由于财政持续扩张,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将很快恢复上升势头,债务与GDP之比将在2028年之前回到疫情期间的高点。从长期来看,各国中央银行可能会面临各方面压力,要求它们放慢货币紧缩步伐,以减轻公共财政负担。中央银行还可能面临政治层面的呼吁,要求它们放开货币政策的“刹车”或提高通胀目标。
不稳定的金融体系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当今世界规模大、节奏快且异常复杂的金融体系并不稳固。此前,市场对显而易见的流动性错配和过高的杠杆防范不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及其他非银金融机构往往将自身置于“极限”境地,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当政策开始收紧时,叠加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的私人债务水平高企与通胀飙升并存情况,金融市场较以往变得更加脆弱。而这都与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激进冒险行为有关。
从最近爆发的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中可以看到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累积影响的痕迹,其根本原因是高企且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与长期处于低位的利率环境相叠加。数十年来,许多主权国家以极低的利率和较长的期限发行了巨额债务,其中大部分被金融机构吸收。对利率将保持在低位的预期塑造了这些机构的商业模式,同时助长了它们的冒险偏好和高杠杆率。这些行为都加剧了激进的期限转换和流动性错配,放大了金融风险。这些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现在都面临着此前未曾应对过的利率突然飙升的风险。
在硅谷银行破产事件中,较为集中且未受保险保护的储户群体发现,该银行投资的长期债券(主要是政府债券)出现了巨额未实现损失,随之而来的储户挤兑和流动性枯竭导致银行陷入困境。而这在美国中型地区性银行中又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连锁效应。在2022年席卷英国的固定收益养老基金风波中,基于负债驱动投资(LDI)策略的基金因国债收益率意外上升而导致对冲产品产生巨额损失,威胁到投资基金的偿付能力并造成流动性紧缺,进而引发了市场对政府债券进行抛售,并造成金融体系剧烈动荡。
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加剧了各国中央银行在寻求恢复价格稳定时所面临的挑战。如果中央银行不得不在更长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种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而进一步大幅收紧政策又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中央银行需要以最后贷款人或做市商的身份进行干预以稳定金融体系——部分中央银行近年来已数次扮演类似的角色。而这会让市场担忧,中央银行可能会因受到外部力量的主导而放弃控制通胀的努力。
造成当前困境的原因
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偏离出安全边界的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制定者高估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引导作用,并寄望于通过足够有力的刺激政策推动来点燃长期增长的引擎,而这就是所谓的“增长幻觉”。具体来说,政策的偏离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当时,通胀的上升被视为重要的警示信号,它意味着相关政策已经偏离出“稳定区域”的安全边界之外。当70年代的高通胀出现后,货币政策制定者采取了上调政策利率等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增加了财政的脆弱性并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消化,通胀下行,公共债务水平趋于稳定,政策重新回归到“稳定区域”之内。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前。一方面,金融体系实现了深度的自由化,从由“政府主导”变成由“市场主导”;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全球化削弱了工人和企业的定价权,对全球通胀形成了压制作用,全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胀不再是测试经济是否过热或趋冷的指标,其警示信号的作用也被弱化和忽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也转移到金融体系的失衡与否上。
从通胀失衡到金融失衡的转变导致了政策空间日见局促。货币政策在经济紧缩期间放宽,以缓冲经济下行;但在经济扩张期间,由于通胀保持低位和稳定,又缺乏“理由”来促使中央银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被迫出手支持金融体系,支持摇摇欲坠的经济,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在此期间,低利率环境使得偿债成本压力可控,从而显得公共债务是“可持续的”。而意外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以及俄乌冲突打破了表面上的脆弱平衡,并造成剧烈波动。
政策需要重新获得腾挪空间,回归到“稳定区域”边界之内。但是在恢复过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又可能互相掣肘。更高的利率将加大财政政策调整的难度;若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财政的疲软将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形成压力,迫使其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宽松。
经验与启示
综上所述,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价格稳定。而从长期来看,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持在 “稳定区域”内。这需要在战略、制度和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
从战略层面看,一方面,政策执行者需要逐渐建立起政策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政策之间需要充分协调,而不至于产生互相制约的政策效果。货币政策方面,继续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然是重中之重。财政政策方面,需要继续健全审慎财政政策的机制,独立的财政委员会和精准的财政规则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制度上,需要辅以健全的微观和宏观审慎框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加强金融体系韧性,监管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但进展并不均衡。银行业的微观和宏观审慎框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非银金融领域却停滞不前,而过去数十年正是非银金融机构规模大幅扩张的时期。此外,最近银行业的动荡局势表明,银行业的监管仍有进步空间。
但从根本上来说,政策制定者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即承认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具有局限性。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过于雄心勃勃,也可能造成巨大损害。“增长幻觉”的谬误表明,要实现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增长,除了加强推动经济的供给侧改革之外别无选择。■
(本文系作者2023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杂志。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中国股市杠杆,风险请自担。

